伊藤 德也
在周作人提出“生活之艺术”以前
在中国提到“生活之艺术”,多指享受生活的各种技巧、秘诀,包含着些许人生哲学的意味。林语堂与梁实秋曾分别著有一部《生活的艺术》,但两者本质上均源自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在提出“生活之艺术”以前,周作人曾对艺术、生活、美、自然、现代、颓废等概念有过反复推敲。艺术,既不等同于美术,亦有别于单纯的技术。生活,既是基于生物学人生观的“生活”,又被其赋予了从自然、现代、颓废等多样化解释中提炼出的独自思考。了解周作人所提倡“生活之艺术”的思想基础,于当今的我们也同样颇具意义。而联系“家”这一主题,与长兄鲁迅决裂这一周氏家族内的私事,无疑是周作人提出“生活之艺术”的背景之一。
[讲师介绍]

核心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文学、主要关于周作人、林语堂、张竞生、鲁迅。从各种颓废(decadence)的样态分析现代中国(从战前至当下)的现代性。曾在北京短期居住,分别是大学院时代(1987-89年)的1年半和2006年度的1年间。
课堂照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位作家。1924年,周作人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活之艺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倡“生活之艺术”,并表达了成为其基础的根本思想和态度。那么周作人“生活之艺术”的主张究竟为何?又从何而来?今天,来自东京大学的伊藤德也教授就为大家带来一场特别讲演,通过追溯周作人1924年之前的思想形成过程来解析他的“生活之艺术”论。
1 何谓“生活之艺术”
在讲座的一开始,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叶琳教授向大家隆重介绍了伊藤德也老师。伊藤老师198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06年曾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日中比较文化论的一位大家。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本场讲座正式开始。
首先关于“生活之艺术”这个词,伊藤老师指出其中蕴藏了深层次的文化史含义。纵览世界文化史,以“生活之艺术”为题的作品或围绕它的讨论可谓众多。比如同样为我们所熟悉的林语堂,就有《生活之艺术》(英文原题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本著作。总之,“生活之艺术”这个概念,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当下都一直被广泛讨论的、极为重要的概念。
那么,将视线聚焦到周作人身上,他的“生活之艺术”论又是怎样的呢?在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周作人认为,
“生活之艺术”的要点在于
美丽且微妙地生活,
禁欲与放纵的调和,
欢乐与节制的并存。
参照古代中国、古代希腊、日本的生活文化以追求新的自由和新的节制,这将成为中国的救国之道。
2 周作人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
接下来,伊藤老师开始探讨周作人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在去日本留学之前,周作人选择了英语,这为他之后接触到英国作家霭里斯的作品打下了基础。而在去日本留学后,他一边大量阅读英文著作,一边对日语和日本文化产生兴趣。这一过程中,中国所没有的日本的生活文化令他感到钦佩。可以说,选择英文和日语,是周作人能够提倡“生活之艺术”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五四”到1922年这个时期,周作人曾苦恼于“人生”与“艺术”的矛盾。“为艺术而艺术”还是“为人生而艺术”?这是在世界范围内,自1988年托尔斯泰著作《何为艺术》出版以来就有的对立和争论。“五四”时期,周作人鼓吹过人道主义,曾与托尔斯泰立场接近。但随后,出于对将艺术“道具”化言论的警惕,他转而欣赏托尔斯泰所批判的波德莱尔;另外1920年的患病与疗养也成为他回顾和反思的契机。1922年左右,他开始将人道主义埋藏在心,提出一些艺术派的意见和批评,开始肯定人生之无价和艺术之自律性两方面,并用“的”来连接“人生”和“艺术”,以模糊它们之间的界限关系。
随后1923年,霭里斯的著作《断言》给予周作人很大影响。比如霭里斯著作中的一篇,《圣弗朗西斯和其他》(St. Francis and others)里关于欢乐与节制并存、禁欲与放纵调和的观念就曾被周作人引用。其次是关于颓废主义。霭里斯英译法国评论家布尔热对颓废主义的著名评论为周作人所重译。这一评论“颓废主义就是完整的作品解体成单页而独立,单页解体成段落而独立,段落解体成单词而独立的这种形式”,描绘的正是“部分的整体化”这样一种情况。基于此,霭里斯提出“颓废形式”的美是部分试图成为全体的冲动之美,而“古典形式”的美是全体支配部分的安定之美。可以说布尔热和霭里斯的观点成为周作人从“人生之艺术”转向“生活之艺术”的重要指向。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部分的整体化”与艺术的自我目的化、无目的化紧密相连。“为人生而艺术”的命题是一种以人生整体为目的、以艺术为手段的纯粹的“古典形式”命题。与此相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命题则是一种排除人生目的,仅以自身为目的的命题。艺术本来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是一种“部分的整体化”。周作人虽没有直接谈及自我目的性、“部分的整体化”,却在作品中流露出他有过相关深刻的思考。比起“古典形式”,周作人更看重自我目的性和“颓废形式”的重要性。1926年他在自我回顾中提到自己热爱艺术和生活本身。这是一种纯粹的热爱、品味和享受,比如在1924年一篇名为《北京的茶食》的散文中就有所体现。这里涉及到中文、日文中“人生”和“生活”的微妙差别。周作人不再说“人生之艺术”,改说“生活之艺术”,正反映了他热爱生活本身的倾向。

伊藤老师强调,周作人这一倾向中虽有享乐主义的一面,却也有“自讨苦吃”的一面。即面对生活中痛苦、厌恶的事情,也不回避,去正式它。这同样是他“生活之艺术”论的组成部分。
伊藤老师还谈及,受霭里斯影响,周作人认同广义的“艺术”的重要意义。前面的内容是基于周作人的内在经验,最后,伊藤老师从外部环境来探讨其“生活之艺术”论的性质。主要涉及的是1923年左右,周作人与徐志摩、陈源,以及他的兄长鲁迅的关系。当时周作人在文章中谈到中国文坛时,提出革命文学派和耽美派(或曰艺术派、颓废派)这两大新潮流。徐志摩、陈源的“耽美派也可归于艺术派,但和颓废派间还有微妙的差异。比如周作人主张扎根于中国现实的艺术的样式,而排斥徐志摩、陈源等追求纯艺术的清高。1923年7月,周作人与兄长鲁迅决裂,这与兄弟二人不同的文学艺术主张恐怕不无关联。“为人生而艺术”、并厌恶颓废派作派的鲁迅,与周作人的“文艺无目的论”和“对普通人的自我表现的肯定”无疑是相抵触的。

围绕周作人“生活之艺术”论的思想及其形成,伊藤德也老师的整场讲座进行了充实的探讨。讲座的最后同学们抓住机会,积极向伊藤老师提问,伊藤老师也耐心给予了解答。这场讲座给我们思考艺术、思考人生、思考生活带来很多启发。感谢伊藤德也老师带来的精彩内容!
文/邱心韵(外院)
图/邱心韵 马瑜(外院)
图文编辑/尹晓静(外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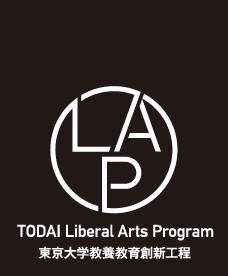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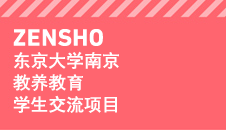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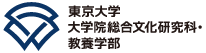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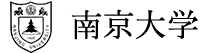



评价内容